技精德诚 永葆医者仁心本色——吴在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原同济医科大学校长。
91岁高龄的吴在德教授有很多身份,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主任医师,也是原同济医科大学校长。他曾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辑及《中华实验外科杂志》总编,是中国肝胆胰外科“突出贡献金质奖章”的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他还是继吴阶平、裘法祖后国家重点医学专著《黄家驷外科学》第七版主编之一,国家统编医学教材《外科学》第五、六、七版主编,当之无愧的医学大家。他历任同济医院外科学教研室副主任,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医科大学校长等,2018年,他刚刚卸任武汉市医学会会长。
在众多的身份和称谓里,吴在德最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吴医生”,不论岗位和职位如何变化,他始终怀有医家的仁者之心:“我是医生,这是我的本职,更是我毕生要保持的本色”。
壹
旧中国末代大学生和新中国首批医学家
吴在德的学生时代正处于中国新旧社会的交替之期,他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当时的学生一起参加过罢课、学潮,后来又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读《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前夕,吴在德曾耳闻国民党当局在同济医学院抓捕进步学生,他不但没有因此而畏惧,相反更加靠近进步学生,同他们一同奋起保卫学校,迎接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济大学回到人民手中,吴在德迅速接受进步思想,1951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回忆这段经历,吴教授十分感慨: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最初只想着光宗耀祖的人变成了一个懂得用医学为人民服务的人!
“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就是这个思想很简单,走上医学路是一个意外,严格来讲,我是旧中国的末代大学生,1948年9月份进大学,进大学的时候,正好是上海‘三反’刚过,我进去的时候,有几次罢课,我这个人经过抗战的,吃过苦的,也被人抓去过,所以民族意识很强,当时很有正义感。解放以前,我还在保卫学校。解放以后,55年毕业,按照同济的规矩应该是七年制,后来缩短了,同时因为要迁校又延长了半年,因此我是春季班毕业的。1948年进大学,1955年3月份毕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解放前只有1/2的时间在上学,解放之后就没断了,所以我读了5年半。我的人生变化就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抗美援朝以前,我是比较正义的,对国民党是不满的,但意识没那么高,后来地下党的一些进步同学就做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看《新民主主义论》。抗美援朝激发我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家绝对不允许别人侵略,我的思想转变,是在抗美援朝,根植于抗战。
抗美援朝是我的转折点,国家绝对不允许侵略,才开始要求进步,我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但是才医学院一年级,就不要我们。当时我们在上海静安区参加当地的学生工作,一边上学一边做宣传,当时我还是个普通老百姓,(组织)就让我负责静安区的教育,上街做宣传,我开始了思想转变,所以我1952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的转折就是在那个地方,以前是一个正义的人,变成一个要求进步的人。”

贰
技精德诚凸显医者仁心
1955年,中央政务院令同济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整体内迁,以加强华中地区医疗及教学力量。吴在德和他的老师们告别上海,来到华中重镇武汉,从此,他的足迹遍布荆楚的山岭乡村、湖汊渔港。近60年来,吴在德教授怀揣希波克拉底誓言,牢记“大医精诚”的古训,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系病患,为人民健康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
外科医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 。面对风险,吴在德医生总是把个人荣辱得失置于一边,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面对越来越多且复杂的疑难疾病,的确需要医生有一定“冒险”精神,但吴在德并不赞成“艺高胆大”,认为“没有厚德仁心做基础,艺高胆大往往是惹祸的根源”。他提倡“三思” 。一是“慎思”,每一项诊疗措施采用前,深思熟虑,进退有度,不良医疗效果的教训常常不是“想不到”,而是“不想到”;二是“反思”,无论一次手术成功或是失败,事后都需要反思。尤其成功后,“再成功的手术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懈怠是最大的危险”,哪怕是一根引流管或导尿管都不可小视;三是“换位思考”,视人如己,视病人如亲人。
一位来自农村的病人,过去巡回医疗时找吴医生治过病,深为他的医术所折服,因为他患有晚期胃癌,又专程来到武汉找吴医生。吴医生热情接待了他,经过详细检查,觉得按当时的技术条件与能力只能姑息治疗,且由于当时化疗药物奇缺治疗效果不会理想。病人丧气地说:“那我明天出院,乘早班船回去”。这天晚上一个个问号使吴在德久久难以入睡,他想:按病情这位病人不久会发生胃出口梗阻,这岂不是宣判病人的“死刑”了吗?假如此人就是我的亲人又该如何呢?病人所乘的船将于凌晨五点半开,他早四点钟赶来病房,用商量的口吻对病人说:“你暂时别走,我再努力一下”,病人喜出望外。吴教授重新给他做进一步检查,分析认为,虽不能根治,但如果手术得当,病人是可以多活一些时日的,于是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手术方案。术后,病人又存活了5年多。 吴教授说:“医生最高兴的不是得一个奖状,也不是奖励多少钱,而是在病人生死攸关的时候救活了他,数十年之后,突然遇到你的病人,互相问候一声, 这是最令人欣慰的。这才是一位医生的价值所在。”
“解放以前,医生是讲仁心仁术,但总体来讲不可能想到为人民服务,这绝对是想不到的,这个是解放以后慢慢培养起来的主观思想上的认识。客观上,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很多不一样了,医院都是国家领导的,设备等各方面都进来了,学习条件也好了, 改革开放以后,步子就更大了。下乡两个体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认为自己本领很大,一下乡就发现不行了,我学的是外科,我的外科还比较全面,都学过,所以认为自己本领不错,下乡以后发现它不是按科分的,什么都得看,就感觉自己本领不行了,第二个感觉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加深了,老百姓太需要医生了,差距太大了。
我是一直反对艺高人胆大的,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四野的副团级干部,到我这儿来,我说你这病我治不了,他说,我打仗四进四出都没打死,我绝对不要死在医院里,你给我开刀!后来我给他开刀了,很冒险,开刀以后,他第一句话是‘吴医生我非常感谢你!’第二句话是‘但是,我的命不是你救的,是我自己救的。’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反思,这个当时非常危险,我的技术争取一下是可以达到的,为什么没有积极想给他开?所以艺高不一定胆大。裘老说过一句话,一个病人来了,你可以做小的(手术)就不要做大的,能做简单的不要做复杂的,艺高和胆大是辩证的。裘老还有一句话‘医生最要紧的是医德医风,只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才能发挥医术的作用’这很辩证,这两者是不均等的,没有技术不行,有技术可以不用,也可以用过头,所以,艺高胆大,很多人爱摔跤,医生绝对不能随便冒险。我赞成的是三思,开刀以前要慎思,做的再好,再有经验也要深思,明天做手术我很熟练了,可能碰到什么问题都要想得很透;开完刀以后,再顺利平安也要反思,我有哪个地方做的还不够,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病人治好出院以后,还要换位思考,假设你是他,他是你,你该怎么做?”

叁
以人为本科研教学围绕病人需求
上世纪50年代初,为适应我国外科发展的需要,在医院支持下,身为外科主任的裘法祖果断地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矫形外科、胸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及麻醉科等专科。1964年经国家批准在国内率先成立腹部外科研究室,交由吴在德负责筹建。腹部外科为外科之基本,在裘教授指点下,吴在德将肝胆外科选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此跟随老师在相关领域拼搏50余载,成果迭出。
1958年同济医院率先在国内尝试器官移植的实验研究,吴在德是我国最早开展临床肝移植参与者之一,并率先总结发表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临床肝移植手术技术系列论文。1979年,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裘法祖任所长,不久吴在德担任该所的副所长。1984年,吴在德教授担起了同济医科大学校长的重任。
进入21世纪,裘老将自己长期担任的两项学术重任交给自己所信赖的学生吴在德:一是全国医学生5年制本科《外科学》教材主编 ;二是《黄家驷外科学》主编。吴在德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外科学》已出第5、6、7版。《黄家驷外科学》第7版也在裘老去世不久出版发行。
一位医生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病人的需求上,这是一种最朴实也最崇高的价值观。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的科技人员,吴在德总把自己的科研课题与病人最急切的现实需求联系在一起。1958年,他搬回同济医院第一台B型超声波仪器,最早开展超声波检查的研究。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他就主攻临床难题:肠粘连预防问题,虽当时许多同事都认为这个领域不会产生太多的研究成果,但为了病人他还是坚持了下来。通过对照试验发现关腹时腹膜缝线的选择对肠粘连的发生有一定影响,这项研究结果挑战了当时临床常规应用的某一理念, 从此腹膜缝合采用了丝线间断外翻缝合替代肠线连续缝合。1963年以后,他回到普外科,主要从事肝胆外科及器官移植临床与科研。为解决病人手术中出血问题,研制了Nd:YAG 激光手术器,并应用于临床肝切除术获得成功。吴在德长期致力于肝内胆道出血的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历经14年,保持对一组(18例)肠系膜上腔静脉--下腔静脉分流术治疗成人门静脉高压的病人随访,克服重重困难,使随访率达100%,对这一治疗方式的效果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为医学界所认同。
“全国五十几例,掀起了肝移植的第一个小高潮,我们做了十三例,我们最长的患者存活了9个月(264天),这是第一波高潮,之后就越来越成熟了。器官移植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器官移植既有临床又有研究,到现在都是这样,而且器官移植我们品种最多,肝移植,肾移植,脾脏移植,胰腺移植到器官大腹腔移植,我们做的都比较多。
教材是裘教授很重视的,那个时候专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讨论,我从第二版开始一直参加下来,一直听下来的,很较真的,一句话一个字的抠。有一次在我们同济医院开会,坏疽和坏死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在那里争论,后来权威来了,跟我们说这两个有区别。裘老特别严谨,我不记得多少文章给他改过,但是我记得每篇文章他都要改。同济我们定的校训,就是8个字,团结严谨、求实奋进,这几个在同济体现的很明显。
(“新中国70年历程,您的人生重要节点有哪些?”)
节点要放在科技大会,1978年,思想解放了,广州会议把知识分子划到了劳动人民,这个过程不容易的,78年是个大转折,大家认为春天到了,78年之后对生产力的含义不一样了,知识分子的脑袋解放了。 要说变化,就是习近平同志当家以后,对发展、开放和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命运共同体这提法太高明了。现在习近平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现在看法完全不一样了。
我认为,进入新时代,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必将比过去更加迅猛的发展。作为同济人,要传承和发扬同济精神,为健康中国努力拼搏,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什么要讲健康中国这个概念?医生和医疗概念太窄了,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健康中国,(大家)已经开始贯彻了,现在中小学跑步等活动已经开始了。所以要看得远,我们只想到预防和治疗,这远远不够,医务工作者不能把自己局限得太小。要为健康中国努力拼搏,做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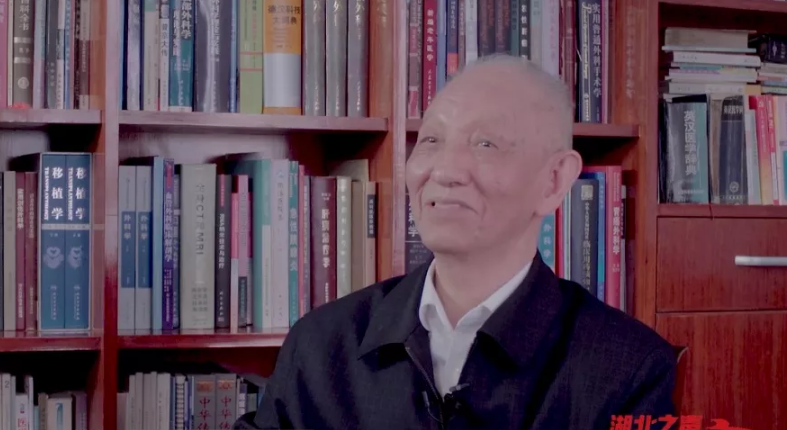
多年来,吴在德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食管癌、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肝移植进行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获得诸多成果。 在他主持或参与的获奖课题中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卫生部科技进步甲等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一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如今,退休在家的吴在德仍然关注科研和教学,每当有年轻医生发表论文前来求教,吴老都仔细阅读,给出中肯的修改建议。“团结,严谨,求实,奋进”,这是吴在德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时定下的校训,而他也始终坚守和践行着这沉甸甸的八个字。
附件:


 鄂公网安备42011102000831号
鄂公网安备420111020008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