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渊 树木树人 一生奉献影像学
1925年11月2日出生上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教授。
简介-郭俊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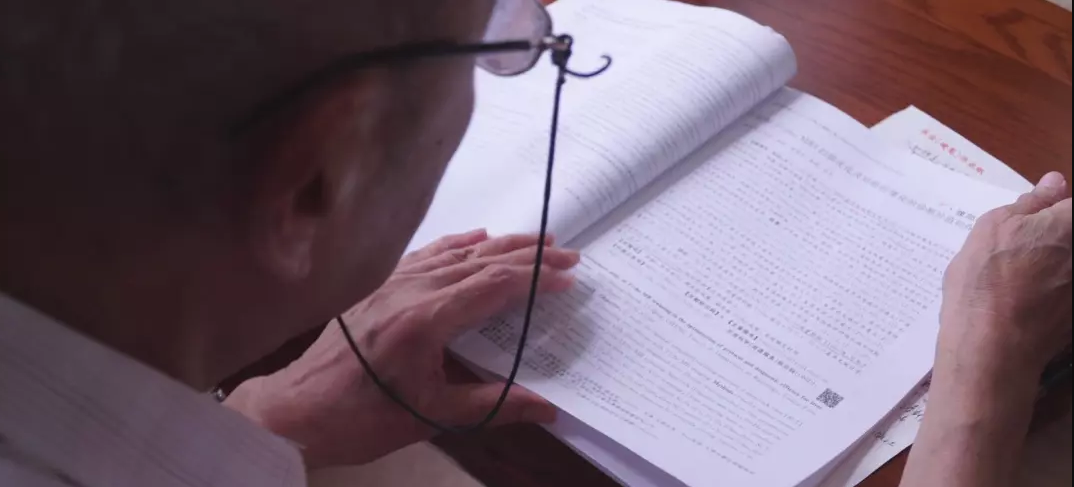
郭俊渊,1925年11月2日出生上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教授。
他生逢战乱年代,阅尽人间沧桑,目睹时代变迁,饱尝苦辣酸甜。在一片处女之地辛勤劳作,影像介入,救死扶伤,编著科研,教书育人,含辛茹苦,为改变穷白面貌求索一生。郭教授曾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影像诊断》的编审,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影像诊断学》第1、2、3版的编写(1982-1995年)。1990年获国家教委颁发奖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阅世间沧桑 一腔热血投身医学
郭俊渊,1925年11月2日出生于上海,汉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刚刚小学毕业的郭俊渊,也关心着战争的发展。从家人和朋友口中,得知了战争的残酷,更看到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从医的种子便从那时开始,深深埋进了郭俊渊的心中。
1943年高中毕业,征求家人意见之后,郭俊渊进入上海德国医学院。进校的时候,学校全部都是德国老师讲课,如果德文不好,就很难听懂课程。所幸郭俊渊在中学就学过德语,读了半年的德语班之后,他就进入了大学一年级学习。
大三那年,抗战胜利,上海德国医学院停办,不再接收其他学生,全部学生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虽然经历波折,但郭俊渊和同学们的学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转眼五个学年结束,第六年就要开始实习。那个时候,对实习医生要求很高,一个人要管5-10张床,负责写病历,做常规检查,每天早上还要去看病人摸脉搏。在这段时间,郭俊渊分别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各实习了2-3个月,眼科、耳鼻喉科也分别实习了一个月。实习期间,郭俊渊受益匪浅,这一年,也成为他最为难忘的学生时代。
“这是在我小孩的时候,印象就比较深刻。那个时候生病都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大家都知道医生很好,可以看病。后来大一点点,家人告诉我医生是个自由职业,这些意见加起来,就觉得考医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就想去考医。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学什么,还要征求大人的意见,对吧,但我还是知道医生是一个好的职业。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蛮用功的,学生很用功,老师也教的比较好,那个时候我们学习都老老实实的,没有那么多诱惑,就是专心读书。那个时候回想起来,那时都觉得跳舞是个不好的事情,当然现在不会这样看了。
实习医生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听课就是听理论课,具体怎么做都是不知道的,他做实习医生,一个医生要管5个到10个病人。不管白天黑夜,反正病人来了,他的一切都是你管的,他的病情变化,他的大小便,都是你要管的,你要检验。现在是开单子去检验科检验,那个时候不是的,没有人做,要自己去看大便怎么样,小便怎么样。所以我认为实习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从这个里面你知道怎么关心病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说你每天早晨去查房,一定要摸摸病人的脉搏怎么样,看看他怎么样,要和病人亲密接触才能够了解病人的情况,我觉得这还是很要紧的,所以这一年时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年,从理论到实践,对以后要做医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2.医疗队磨砺 大爱之心关怀病人
1949年6月,郭俊渊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校附属医院(当时名中美医院,同济医院前身)放射科工作,师从荣独山教授和沈成武教授。
新中国建立前后,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打响,作为最早投入这场战斗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宁、沪、杭地区,5月下旬,毛泽东责成第三野战师副司令员粟裕组织部队进行攻台准备,部队在近郊江苏太仓做战前准备。这里紧靠长江口,湖泊众多,是训练渡江作战的理想场地,然而这里也是血吸虫病疫区,血吸虫病、疟疾等频发。军队卫生部门虽有防范,但这支擅长北方作战的部队对此认识不足,加之攻台战役重于一切,水上训练日以继夜,每名战士一天至少两个小时进行游泳训练,到了9月中旬,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一时被称之为怪病,引起了部队重视。中美医院(同济医院在1945-1951年的称谓)院长林竟成派医师邵丙扬等专家赴太仓等地驻地普查。确定病因后,上海全市抽调医务人员组成上海血防大队,同济中美医院的邵丙扬医生被任命为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其中太仓中队由同济医学院组成,队里有十几个小组,郭俊渊是第三小组的小组长,还有一位实习医生做副组长,小组里还有11个医学院各年级的学生,共13个人负责一个炮兵营的三百多个病人。主要负责给病人体格检查,摸摸脾脏,听听心,再就是打针,做治疗,偶尔做一些健康宣教。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郭俊渊这一组负责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疗。完成任务后,太仓中队许多人都立功受奖。
1951年,郭俊渊参加了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由于病人都从前线回来,各种伤都有,郭俊渊等帮助检查、治疗病人,同时在长春军医大学进行教学工作,提高医务人员的水平。
当时长春军医大学的放射科设备比较差,也没有专科医生。郭俊渊到长春后,长春军医大学意识到放射科的重要性,于是从内科、外科和五官科分别抽调一位医生跟郭俊渊学习放射学,这些医生后来都为自身领域发展放射学作出了积极贡献。
“毕业以后参加工作,1950年就参加血防了,我记得是1月5号,因为解放军在太仓训练,准备去解放台湾,解放军都是陆地军队,江河作战比较少,所以他们要去划船游泳,所以大量的解放军感染了血吸虫病,所以解放台湾就受到了影响。就组织上海的一些医务人员去给解放军治病,那个时候病人很多。我们同济成立了一个队,上海医学院成立了一个队,上海市卫生局的医院成立了一个队。同济这个医院有小队长、小组长,小队长是内科的医生,组长就是我们年轻医生,副组长就是实习医生,再下面就是五年级四年级三年级的学生。
我是第三小组的组长,我就管一个营,一个炮兵营,大概也有两三百人,他们住在一起,我们去给他们做治疗,打针,同时也观察锑剂对心脏有没有什么改变。我这个组,幸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比较平安,我们好像治疗了300还是100个病人,每天去打针,还要观察病人身体好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和解放军亲密接触,就觉得解放军确实纪律方面做得很好。
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对我、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亲密的接触了解放军,解放军的思想水平比我们高一些,我们给他们治病,就体会到他们的一些优良的传统,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都还是很高兴的,我们都很高兴很愿意参加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951年抗美援朝了,我是年轻医生,又是男性,应该要去的,我们都很自愿自觉的报名参加,我们没有过鸭绿江,没有去朝鲜,就在长春的医科大学。当时他们医疗水平不是很高的,我去了以后,帮他们做检查,同时去培养人,他们自己也晓得放射科基础比较差,他们一共有4个医院,内科医院,外科医院和普通医院,他们抽人来学习,我那个时候毕业才两年,但是比他们懂得多,所以除了医疗以外我还给他们讲课,(我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医生,懂得很少,但是比他们懂得多。我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跟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最后他们给我评了两小功。
我的学生中间,到后来我才晓得,有一位后来当了长春放射学会的主任委员,这说明我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受到锻炼,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共产党、解放军。
3.举家迁汉 助力放射科交流发展
1954年,同济医学院率先西迁到武汉,由于教学力量不够,郭俊渊被派到武汉来担任教学任务。郭俊渊服从组织安排,退掉了上海租住的房子,带着子女们的外婆、妻儿义无反顾的举家搬到武汉。
当时,郭俊渊刚刚升任讲师,医院分配的宿舍有两间房间,一个小厨房,还有一间很小的卫生间。更令他感到振奋的是,当时同济医院的放射科有四台设备,比上海中美医院更好,这也为郭俊渊开展科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5年到1966年,国内形势较好,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在裘法祖教授带领下,同济的外科也快速发展,由于放射科跟外科的关系较为密切,外科发展必然推动了放射科的发展。50年代,郭俊渊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四肢动脉造影和腹主动脉造影,在“中华放射杂志”发表论文。
70年代起,郭俊渊主攻腹部放射学,尤其是胃肠道和肝脏影像诊断。1981年郭俊渊赴联邦德国进行校际交流,回国后组建介入放射学组,成为国内率先开展肝癌介入治疗单位之一,他和同事们一起改进治疗技术,多次举办学习班,将有关新技术向省内外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上海搬到武汉以后,已经有大的变化了,房子好了不说,设备也好了很多,但是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也没有变,一直都传承下来的。
“放射科刚到武汉的时候,仪器设备比上海都要好一些,那个时候武汉也在发展,建桥修路,那个时候车祸和外伤比较多,脑外伤很多的。那个时候做了不少,但最后没有写文章,为什么没有写文章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那么多病例,没有超过上海,重复人家的东西,没有意思的,再后来到动脉照影,做的比较好,后来才写了些文章。是为了病人而做,而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做,病人需要做,做了以后我有什么经验和体会,我把它形成文章,后来在中华放射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关系,后来派人去德国进行校际交流,同济就派我去了,从那里看到了新的检查方法,介入放射学、动脉穿刺以后插管,打化疗药,治疗肿瘤等这一套东西我就学到了。他们让我在他们的病人身上做,一般不让的,看我还可以(笑)
学会以后回来,就让年轻医生做,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你们去做,你们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们兜着!所以我就很愿意培养医生,我们在同济建立了放射学之后一直在发展,就不是一个人了,就越来越多了。
放射学里面我们不是有一本杂志吗?最早是翻译的他们的杂志,到最后就跟他们脱钩了,因为我们的病例也很多了,领导非常支持,现在这本杂志上不光是同济,还有其他的很多单位都参加进来了。
我想作为医生来讲,一切为了病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诊断搞清楚,同时不能损害病人的身体,影响他人。另外,放射科医生要向临床医生学习,他对病人的了解要比你多,要和他们商量学习。
当然最后还是要一切为了病人,病人能够早一点恢复健康!
我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希望我们的老百姓越来越幸福,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地方比较贫困,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要扶贫,要消灭贫困,我都非常赞成,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的科学水平等等都要赶上去,不能什么东西别人做好的我们来用,我们要自己发明、自己创造,要让别人用我们的东西,这样就比较好了。”
历年来,郭俊渊和同事们撰写了数十篇科研论文,总结医疗科研成果,发表于《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临床放射学杂志》等刊物上。部分文章发表于国外杂志。1989年郭俊渊和同事们获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及武汉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2010年9月,郭俊渊在广州接受2010年第九届全国介入放射学术大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附件:


 鄂公网安备42011102000831号
鄂公网安备42011102000831号